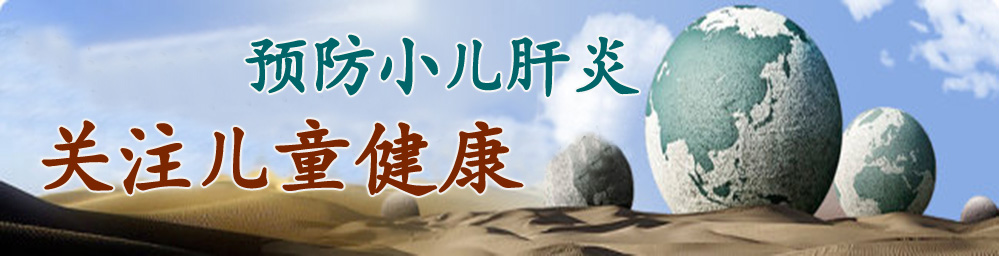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的心血管损害研究进展
本文原载于中华传染病杂志,,33(08)
HCV感染后有发生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危险。既往由于未考虑到HCV感染后非肝脏的结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被低估。最近,其他HCV相关性疾病也逐渐有报道,包括循环系统、泌尿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精确评估作为系统性炎性反应的肝外表现,可显著提高对其病理负担重要性的认识,更强调有效抗病毒措施的必要性[1]。尽管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慢性HCV感染是促进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等的证据亦越来越多[2]。现就HCV感染与相关的心血管损害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HCV感染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不论是亚临床的还是显性的,都是一种慢性炎性疾病,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冠状动脉性疾病(coronaryarterydisease,CAD)、卒中和肢体缺血,除传统的因素外,其他新的因素也被认为可能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CV感染与冠状动脉、脑动脉和颈动脉粥样硬化高发病率有关[3]。
HCV与CAD之间显著的相关性在一项群体研究中得到证实。Butt等[4]研究发现,在校正传统危险因素后,HCV感染发生CAD的风险比(hazardratio,HR)为1.25(95%CI:1.20~1.30)。另一项研究发现,HCV感染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Reardon严重程度评分)的独立预测指标(OR=2.,95%CI:1.~2.;P0.01)[5]。一项中国台湾对例4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的研究发现,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甚至HCV感染的比例在缺血性心电图组较非缺血性组显著升高;多因素分析发现,HCV感染较非HCV感染发生缺血性心电图的危险增加1.倍[6]。HCV感染者既往缺血性心脏病发生率更高(P=0.)[7]。但也有研究发现,HCV与缺血性心脏病无相关性[8]。德国一项包含例抗-HCV阳性和例对照组的一般人群研究,也未发现HCV血清学阳性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9]。
对相关文献进行的Meta分析支持慢性HCV感染是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显著增高的危险因素[10]。HCV感染者CAD发生的危险性增加[11]。但英国的一项随访3.2年的研究并未发现HCV感染与发生心肌梗死之间有相关性[12]。另一项系统性回顾分析发现,HCV感染与CAD之间的相关性不明确,因为一项大样本人群分析发现HCV感染使CAD的危险性降低(校正后的OR=0.74;95%CI:0.71~0.76),而另外的研究则未发现HCV和CAD之间有相关性[13]。
HCV感染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清楚,通过几种直接和间接的机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和并发症的发生,包括HCV在动脉壁的定植和复制、肝脏脂肪变和纤维化、促炎细胞因子分泌的增强和失衡、过氧化应激和内毒素、混合性冷球蛋白血症、细胞和体液免疫的破坏、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低脂联蛋白血症、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组成部分[14]。有证据显示,血清HCVRNA水平与颈动脉硬化呈独立相关性,且在抗-HCV阳性患者颈动脉粥样斑块中检测出HCVRNA,甚至仅在粥样斑块中检测阳性而血清中阴性,提示HCV在斑块中复制,在局部对动脉壁产生直接损伤[15],HCV还可能刺激合成促炎细胞因子,促进粥样硬化发生[10,16]。
理解这些复杂的机制对于开发预防和治疗慢性HCV感染血管并发症的新方法非常重要。目前干扰素和利巴韦林联合清除HCV可显著降低肝脏相关疾病的病死率。由于目前应用方法和以前评估参数的不同,很难获得一个HCV与CAD之间相关性的确切结论。需要设计良好的前瞻性研究和Meta分析研究加以确定。目前,HCV感染对心肌梗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尚不能进行Meta分析。
二、HCV感染和心肌疾病
Saleh等[17]的研究显示,HCV组QTc间期较对照组显著延长,且在无易感因素的情况下超声心动图显示舒张功能异常,可能是由心脏慢性炎性反应和轻度纤维化所致。平均B型利尿钠肽(N-terminalpro-brainnatriureticpeptide,NT-proBNP)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g/mL比(32.7±21.2)pg/mL,P0.01]。另一项研究也显示,NT-proBNP浓度在HCV感染者较对照组显著升高[(71.6±79.1)pg/mL比(9.8±24.4)pg/mL,P0.05][18]。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可能影响NT-proBNP的参数后,慢性HCV感染与NT-proBNP水平呈独立相关性(P=0.)。因此,慢性HCV感染可能影响心肌功能。
NT-proBNP是血管紧张度、水电解质平衡和心血管生长强有力的调节因子。通常来说,在病理生理条件下,如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NT-proBNP的分泌显著增加,其在慢性炎性反应过程中分泌也增加。因此,其升高可能与HCV感染所造成的慢性炎性反应有关。
一项研究显示,在HCV感染组,右室面积变化分数(RVFAC;31%±10%比48%±12%,P0.01)、三尖瓣环收缩偏移[tricuspidannularplaneexcursion,TAPSE;(13.5±1.5)mm比(19.2±3.4)mm,P0.01]和右心室收缩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8.3±1.1)cm/s比(17.7±3.3)cm/s,P0.01][19]。右心房[(4.8±1.3)cm比(3.6±0.6)cm,P0.01]和右心室内径也显著高于对照组[(4.4±0.8)cm比(3.3±0.5)cm,P0.01],另外,收缩性肺动脉压[(36.3±9.9)mmHg比(23±7.8)mmHg,1mmHg=0.kPa,P0.01]和肺血管阻力也高于对照组(3.5±1.1比2.1±0.8,P0.01)。HCV感染与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异常、心律失常可能也具有相关性[20]。Cavalli等[21]报道,1例HCV相关的血管炎患者经胸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室肥厚和弥漫性运动功能减退,在用抗-CD20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后,心肌肥厚和收缩功能逐渐恢复。
一项研究发现,9%的慢性HCV感染者有心电图异常,87%有严重程度积分(severityscore,SS)异常[22]。与治疗前SS异常相关的独立因素包括组织学活动积分、血清HCVRNA和靛氰绿清除率。在干扰素治疗后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的患者SS改善和复发患者中,HCVRNA在最初消失的患者SS改善,随着HCVRNA的再出现,SS增加,在干扰素治疗无应答者,SS无改变。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干扰素抗病毒治疗过程中也可以引起心肌病变[23,24],需要与HCV引起的心肌病相鉴别,在停用抗病毒治疗、短期治疗心力衰竭和支持治疗后,心肌病变症状逐渐缓解。
三、HCV感染与卒中
HCV感染后肝纤维化越严重,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危险性越高,尤其是基因1型HCV,且检测到HCV在颈动脉粥样斑块和大脑内皮细胞中复制[25]。因此,可以推测HCV是卒中的高危因素。研究发现,HCV感染的流行率在卒中组高于对照组(26.8%比6.6%,P=0.);多因素分析显示,HCV感染是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OR=2.04,95%CI:1.69~2.46;P=0.)[7]。对新发生的卒中患者,校正年龄和性别后HCV感染者较非HCV感染者的风险增加(HR=1.23,95%CI:1.06~1.42,P=0.)。干扰素为基础的治疗(interferon-basedtherapy,IBT)可显著降低HCV感染者发生卒中的危险(调整后的HR=0.39,95%CI:0.16~0.95;P=0.)[26]。但也有研究发现,HCV与缺血性卒中无相关性[8]。
将来应以大样本人群为基础的队列研究来证明这个结果,同时需要评价不同基因型HCV感染对卒中的影响,对最新研究结果进行Meta分析,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并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27]。
四、丙型肝炎相关异常代谢综合征(hepatitisC-associateddysmetabolicsyndrome,HCADS)
已被大家熟知的是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均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除了已知的胰岛素抵抗危险因素外,慢性丙型肝炎(chronichepatitisC,CHC)也与胰岛素抵抗(OR=2.06,95%CI:1.19~3.57)、糖尿病(OR=2.31,95%CI:1.18~4.54)和高血压(OR=2.06,95%CI:1.30~3.24)呈独立相关,CHC也与充血性心力衰竭独立相关[8]。有研究发现,约6%的HCV感染者有脂肪性肝炎,HCV脂肪变发生在有多重代谢异常的背景下(高尿酸血症、可逆性低胆固醇血症、胰岛素抵抗、动脉性高血压和内脏脂肪组织的扩大),总称为HCADS[17]。在包含名人群的研究发现,CAD的发病率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fattyliverdisease,NAFLD)患者中最高为7.4%,在病毒性感染和酒精性肝炎患者CAD的发病率则无差异[28]。
HCV脂肪变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证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成熟[29]。因此,推测CHC可能通过与代谢综合征相关,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险性,但如前所述HCV感染与心肌梗死危险性增加无相关性[11]。可能的机制包括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显著降低,凝血系统缺陷,心肌功能受损,静脉回流和中心静脉压降低,NO和TNF-α水平升高,心脏β受体信号转导消失等,所有这些因素对预防发生心脏缺血和CAD有保护作用,这些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30]。
HCADS的表现在所有HCV基因型都存在,在基因3型HCV感染伴NAFLD患者,似乎通过溶酶体三酰甘油转运蛋白、过氧化物酶增生激活受体-α、固醇调节因素结合蛋白等更大的变化来增强脂肪变的分子机制[23]。另外,病毒直接和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而且,整个HCV生活周期与脂质代谢相互作用,病毒性脂变与代谢性脂变重叠,HCV诱导的代谢性疾病促进肝纤维化的进展。随着感染时间的延长、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发生、血液中过氧化应激和炎性产物的聚集,直接或间接或两种方式均存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31]。另外,HCVRNA可能通过代谢微环境异常促进动脉粥样硬化[15]。
过去认为肝硬化对CAD有保护作用,但最近的研究评估了等待肝移植的肝硬化患者无症状CAD的发生率,多层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在65例患者中,58%有轻度CAD,34%有中-重度CAD[32]。
五、HCV感染和急性心包炎
Kocaman等[33]报道,1例65岁的女性患者因胸痛、呼吸困难和乏力收住院,其3个月前曾有拔牙史,未服用任何药物治疗,超声心动图显示心包积液,血清ALTU/L,ASTU/L。HCVRNA15×IU/mL,基因型为1b型。考虑为HCV感染引起的急性心包炎,给予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1个月后心包积液和相关症状消失,3个月后HCVRNA阴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HCV感染可引起急性心包炎,干扰素抗病毒治疗也可引起急性心包炎,接受干扰素治疗的患者如主诉有突发性胸痛,首先要行心脏超声检查以明确是否有心包炎[34]。
六、HCV相关混合型冷球蛋白血症性血管炎(mixedcryoglobulinemiavasculitis,CryoVas)
在HCV相关的CryoVas中心脏表现较少见,在例HCV相关的CryoVas患者研究中,7例(4%)出现心脏表现,胸痛和心力衰竭是主要的表现,5例患者心脏影像学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1例为肥厚型心肌病[35]。在多因素分析中,有心脏表现者更常出现B细胞型淋巴瘤(OR=18.1,95%CI:2.8~.7;P=0.)和胃肠道症状(OR=14.6,95%CI:2.0~.9;P=0.)。所有的心脏表现在用糖皮质激素和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消退。尽管早期结局良好,但较无心脏表现者生存率低,随访9个月时,3例患者死亡。
七、HIV-HCV共感染与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disease,CVD)
研究发现,在进行HAART时,HIV-HCV共感染患者较HIV单独感染者发生CVD的危险性有增加趋势(HR=1.44,95%CI:0.97~2.13,P=0.07),从而支持合并感染者应同时启动抗HCV治疗[36]。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在HAART时,HIV-HCV共感染不仅显著增加CVD的危险性(P0.),而且增加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37]。最初认为,这种危险性的增加是由于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相关的代谢异常引起。最近认为是艾滋病本身引起的炎性反应、免疫系统激活和内皮功能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促进因素[38]。
但Kakinami等[39]研究发现,CVD的危险性在HIV-HCV共感染和HCV单独感染者相当,但均较一般人群增加。HIV-HCV共感染和HCV感染者弗莱明汉危险积分(Framinghamriskscore,FRS)分别提高2%(P=0.03)和2.4%(P0.),血管年龄分别提高4.1年(P=0.01)和4.4年(P0.)。且尽管HCV-HIV共感染较HIV单独感染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solubleintercellularcelladhesionmolecules,sICAM-1)和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cularCAM-1,sVCAM-1)水平增加,但用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或颈动脉内-中膜厚度评价的亚临床动脉硬化无明显证据[40]。
八、展望
目前HCV和CAD之间的相关性仍不确定,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与样本量大小、目标人群和研究设计有关。需要更大样本、长期的群体前瞻性研究和Meta分析研究加以确定。将来还需要进行设计良好的研究,用于评估HCV感染对不同CVD的影响和不同基因型HCV感染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无论怎样,医师应意识到心血管疾病可能是HCV感染的并发症。
(参考文献:略)
更多精彩尽在中华传染病杂志
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便宜北京白癜风治疗专科医院
转载请注明地址:
http://www.fbmgc.com/zcmbwh/89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