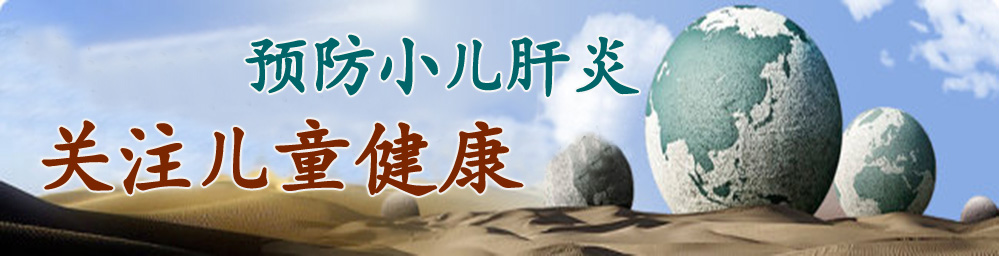一百年来,在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影响下,中药的研究,主要是从化学成分的角度进行探索,寻找和提纯“有效成分”,进行临床验证,做了大量的试验,也出现了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一系列的成就,丰富了临床用药。但是这与中医用药的方法不一样,也误导了中医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医“异化和西化”。中医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能继续这样,沿着“废医存药”,“废医验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吗?
王群才老师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毫无疑问,中药富含着各种化学成分,但是不能用成分说事,中医不是用成分指导临床用药。那么,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性味归经背后的学术原理是什么?有人说,说不清。这不对,中医能说清楚。这是象,用时空之象,代表药物的作用趋势,与人体的复杂调节相适应,就能安全有效地解决人体养生治病的复杂问题,不是用数字。药物的精确度,与人体的精确度,都是不可穷尽的,只有象思维,才能执简驭繁,游刃有余。这是中医几千年,练就的大智慧!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载了中药的起源,而中药在我国实际使用的历史,有资料可证实者也已有几千年。中药曾经从单味药的使用,逐渐发展到复方汤剂治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用什么理论指导人们使用中药,曾经困惑过聪明的古人。《尚书》“药弗眩瞑,厥疾弗瘳”的记载,尚属于经验用药;孔夫子不敢尝季康子送给他的药物,也是缺少有关经验,怕引起不良反应。但是,逐渐地,在漫长的实践中,人们观察出某些药物的功效与毒副作用,积累了化毒为药、变废为宝的经验与使用中药的理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汤液经法》和许多方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十二病方》,以及其他的出土古医方,使我们看到在汉初之前,古人就大量使用方剂治病。而记载药物的《神农本草经》形成于汉代,只能说是形成药物学的著作比较晚罢了。《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药物七情”,说的就是不同的药物相互配伍,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有的互相协同增效,也有的互相制约毒副作用,也有的一起使用会增加不良反应或者产生毒副作用,这种互相配伍之后出现的现象是有规律的,在第一本药物学著作里记载这些方剂学的内容,也可以证明方剂学的起源是很早的事情。《史记》记载了最早接受“禁方书”的扁鹊,可见使用方剂的历史在春秋之前,至于商朝的宰相伊尹是否发明了汤药,我们只能存疑待考了。
自从《神农本草经》和《素问》讨论了组方原则之后,中医使用中药治病,逐渐以复方取代了单味药物,并建立起来一套理论,到金元时期的性味、归经、报使学说的形成,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乃亡”,说的都是汤药治疗的注意事项,已经不是单味药的寒热温凉了。当然,直到唐宋时期仍然有大量的方剂学著作的搜集整理,说明了方药治病经验的积累仍然很重要,并没有因为理论学说、理论著作的出现而停滞。可见,中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经验医学的意味。在近代中医脏腑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被否定之后,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中药,希望通过“废医存药”吸收古人经验。但是,如何吸收,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中医药的理论,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直到现在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但是,背弃中医的中药理论,已经带来了中医创新能力的窒息,按照现代西药的路子管理中药,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至今没有丝毫改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力量进行了大规模资源调查和资料的搜集。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反映在全国和各地中药志或药用植物志、动物志等著作中。现已知中药资源总数有种,其中药用植物种,药用动物种,药用矿物80种。在中药资源调查基础上,一些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萝芙木、安息香、沉香等已在国内生产。中药资源保护、植物药异地引种、药用动物的驯化及中药的综合利用也颇见成效。西洋参、天麻、鹿茸、熊胆和人参、钩藤等就分别是这些方面的典型事例。
中药的现代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①中药的基本理论得到了系统、全面整理,对药性、归经、十八反等作了大量研究,十八反的实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难度较大,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②生药学和中药鉴定学,在中药鉴定方面除一般来源、性状鉴定外,还普遍采用显微、理化等手段。而且鉴定技术已向用少量检品达到迅速、准确的方向发展。③通过中药炮制技术与原理的现代研究,中药炮制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对许多中药的炮制、作了改进和规范,并采用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提高了饮片质量。④建立了中药化学,对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数常用中药明确了主要有效成分,部分弄清了化学结构。⑤建立了中药药理学。对多数常用中药的药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解热、利尿、降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药物筛选。过去不被注意的多糖类、鞣质、氨基酸、多肽等,现己发现有多种生物活性。它在阐明中药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随着中药制剂的发展,新剂型的增多,以及质量检测控制手段的提高,中成药生产已走向现代化。
为了统一制定药品标准,卫生部及早成立了药典编纂委员会,后改为中国药典委员会,于年、年、年、年、年和年先后出版发行了六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年开始,药典分“一部”、“二部”编写。“一部”为中药部分,主要收载中药材、中药成方制剂,另有凡例与附录的制剂通则、中药检定方法等。所收载的中药各版均有调整。年版药典“一部”共收种,其中药材、植物油脂等种,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种。有关中药内容,根据品种和剂型的不同分别依次列有:中文名、汉语拼音与拉丁名、来源、处方、制法、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定、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规格、贮藏、制剂等。附录的内容以及先进的检测方法等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国家一直重视药政法的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了多个有关中药的管理办法,并于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①。可是,这个药品管理法对于中药的管理思路,是比照西药制定的,对于中药的特殊性缺乏认识,限制了中医药的创新能力,急需修改。
中医药教育、科研事业有了空前发展。中国现有20余所中医学院、药学院设有中药专业,近60所医药学校、卫校设置了有关中药的专业;国家一级和许多省市成立了中医药研究院所。在开展科研和人材培养(含药剂士、学士、硕士、博士、工程师、药师等)等方面发挥了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每提及中医药现代化,人们总喜欢拿日本的“汉方”来比较。在国际市场中,日本的“汉方”占了很大比重,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仅占了不足5%,许多穿了“洋装”的中药还大量出口到我国。今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梅万方教授指出,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对中医药的原创贡献,只是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包装。仔细研究日本的“汉方”之路,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日本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都热衷于对中药(包括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天然药物”,而并不重视对汉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
回顾我国近年来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也在走“汉方”之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楚中药的有效成份,分离、提取后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期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认为,中医和中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仅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最多只能称之为“植物药”。
20世纪30年代以前,虽然我国生产大量麻黄,但药品麻黄素的使用一直依靠进口。年陈克恢分离出左旋麻黄硷,年发表了《麻黄有效成分左旋麻黄硷作用》论文,引起了医药学界的重视。赵燏黄先生于年留学日本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药科深造,年回国后,认为我国是产麻黄大国,但麻黄素却靠进口而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于是在北京期间,投入大量精力,潜心研究麻黄素提取工艺并获得成功,改写了我国进口麻黄素的历史。
但是,“中药”与“植物药”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依靠中医理论指导。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学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
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即“辩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例如,日本厚生省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
与轰轰烈烈的中药现代化相比,近年来我国中医现代化却显得十分沉默。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更多偏重于中药现代化,而轻视了中医现代化,国家为中医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远远少于西医,古老的中医正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险。据统计,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39万人,而中医只有40.72万人;西医院有1.68万个,医院只有0.26万个。医院的医院,甚至购买一台先进的仪器设医院全年的投资,为了生存,医院不得不开西医门诊搞创收②。
“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理论现代化,”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施杞教授无不担忧地指出:“如何传承我国中医学理论,包括其中丰富的学术流派,目前已成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医大夫”,很难担当传承我国中医理论的大任。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课程的设置和编排都是参照西医,现有的医疗体系也要求执业中医师要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因此,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在医院校,西医的课程已占到总学时的三成,中医课程只占四成,其余近三成为公共基础课程,外语的课时比古汉语还多,这种西化教育导致许多学生很少有时间、有精力看中医的经典书籍,医院校甚至将《内经》等经典著作,列为学生的选修课。
此外,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医院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而中医教科书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就显然违背了中医理论对“血”的理解。因此,按照这种西医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几乎不会按中医思路看病,转行的很多。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0人,大多数中医已经严重西化,很难称为中医了。
近年来,中药市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劲增长,目前全球总成交量已超过亿美元,占整个植物药市场的六成以上,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而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介绍,我国的中医药只是“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我国每年7.2亿美元的中药出口额,仅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0.3%;而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至今还一个都没有。
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了被全球化和现代化“边缘”的危险。但如果从中医中药产生的文化根源来看,我国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医药中心。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时至今日,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都可以依赖中医;中医药在治病之外,还有一整套保健养生的中医理论,由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常见的中医养生之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西方国家对中医中药的了解,远不如我国,因此,对于中医中药我国最有“发言权”。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已经深陷怪圈:用西医的模型要求中医,用西药的标准要求中药,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二流的西医人才,中医医院,这样的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究员严仲铠也认为,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不能“削足适履”,我国一方面要自主制定科学的中药标准规范,让世界跟我国接轨,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让国际医药界了解中国数千年中药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经验,使世界各国在制定生产质量标准时多参考,接受我们的标准。
事实上,我国有13亿人口、有9亿农民,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优势,为我国的健康事业服务,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医疗健康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发展国内中医医疗市场,是否应该是比出口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广大农村利用中医药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最为成功的经验。当时村村都有医务室,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赤脚医生只有几支银针和一把草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而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农村这些深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早已经荡然无存。在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中医药的作用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一些符医院都列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许多中成药和中草药也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国家卫生部门正大力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开展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组织中医药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农民选择运用中医药预防和诊疗疾病。
中药与中医之间的联系不能割断,一旦走“废医存药”的路子,就会走上“废医废药”的不归路。恰如贾谦先生所说,没有中医理论指导,中药就是一堆垃圾。
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十几年前开始从事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白癜风初期能治好吗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
转载请注明地址:
http://www.fbmgc.com/zcmbwh/160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