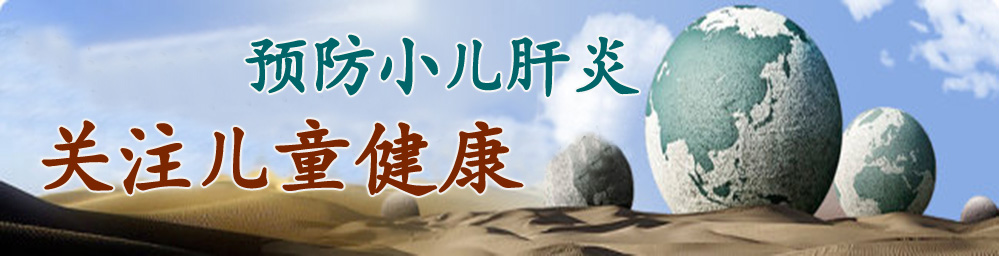在医学层面上
丙肝基本上是“可治愈”的
但在经济层面
丙肝竟然像绝症艾滋病、恶性肿瘤一样
治疗方案,有时遥不可及
◆◆◆
寻药:患病者的光阴
感觉时间不多了。
呕吐、无力、面色无光、满头是汗……周末,在女儿驱车带领下,这位老人决定到浙江普陀山的佛寺里祈福。没想到,车开到一半儿,老人就犯恶心,下车后,一次又一次地吐。女儿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减少颠簸中的振动。最终,女儿放心不下,只能折返回上海家中。
祈福之旅没有成功。身体,仿佛正在漂离生的彼岸。
年夏天,在使用长效干扰素治疗方案一年之后,张美华(化名)决定放弃治疗,把省下的医疗费,留给自己的儿女。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中叶集体主义时代、或者怀有民间信仰的中老年人,这是晚期疾病患者的普遍选择——当家庭收入水平无法负担价格昂贵、疗效不确定的药物时,他们宁可选择“驾鹤西去,福荫子孙”。
省下药钱之后,张美华开始沉迷于一些模棱两可的“理财产品”。每次看到小广告上出现“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字眼或吆喝,她那发黄的眼睛(黄疸)仿佛出现了光亮。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本金还在投,月息取不出,电话打不通……一辈子的积蓄都打水漂了。
这一年的除夕夜,家里没有做年夜饭,桌上摆满了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筷子。张美华面无表情地看着正在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电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春节是短暂的,家的感觉是短暂的,甚至生命都有可能短暂得如同桌上的一次性用品,随时被带走,被废弃。
但对医疗行业有所了解的女儿知道,母亲张美华并没有患上任何一种绝症——既不是艾滋病,也不是恶性肿瘤,她只是一名丙肝患者。而与丙肝并列的乙肝,甚至已经被当做慢性病来治。
恰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教授,正在从事“十二五”时期(-年)的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课题研究。他团队的结论是:在医学层面,丙肝基本上是可治愈的。
魏来曾赴美参加美国肝病年会。在会场上披露的一项来自美国退伍军人数据库的研究显示,共例丙肝患者接受了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DAA)药物治疗,其中即使是针对难治型基因1型的丙肝患者,持续病毒应答率(SVR)也高达92.8%。
那么,张美华为何持续用药一年,没法治愈?
实际上年以前,美国的口服DAA药物并未在中国获批上市,中国患者要想拿到药,要么乘坐国际航班不远万里到美国看“洋大夫”、吃“洋人药”;要么在国内跟海外非法代购的“黄牛党”,挥重金买药。
对于已经退休的张美华,和在上海处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女儿,两个方案不是有难度就是不靠谱。张美华起先只能选择接受长效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这种治疗方案在中国一度被称为丙肝治疗“金标准”,但随着全口服DAA类药物在国外的陆续上市,这个所谓的“金标准”愈发不合时宜。
中国首部《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起草人、中国工程院庄辉院士透露,长效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有很多缺点:第一,患有精神性疾病、血液疾病和肝功能失代偿的丙肝患者不能使用,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也需要慎用;第二,副作用太大,很多患者因严重副作用,不得不终止治疗;第三,部分患者使用这种治疗方案没有效果。
最让张美华母女揪心的,则是价格和疗效,一年六七万的治疗费用,持续一年治疗开销加上“理财”资金被骗,即便有部分纳入医保报销,感觉手头拮据的同时,更对疗效心灰意冷。
指缝中,光阴如流沙般逝去……
◆◆◆
寻路:疗愈者的光阴
过完那个死气沉沉的春节,女儿决定放手一搏——送母亲去国外治。
她开始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上网搜索世界各地最新的丙肝治疗方案。一叠叠打印资料点燃了希望的火苗,但和在老家养病的母亲每打一通电话,微弱的火苗又熄灭了——要不就是价格太贵被母亲竭力劝阻,要不就是母亲的病情并不适用于该方案。
年4月,女儿接到了北京一位医生朋友的电话,对方告诉她有一项DAA新药临床研究,正在招募临床试验的入组患者。如果获选进入这一试验,意味着母亲张美华可以抢先一步,接受美国创新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重要的是——这是免费的,也是完全合法的。由于这一药物已有在欧美获得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临床效果,也在日本等亚洲(东方)人种得到验证,女儿相信,这次临床试验不会有什么大风险(如药物不良反应)。
药还没试,母亲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夜色笼罩下的上海火车站,女儿看到,母亲被诊断出丙肝以来,第一次露出了并不勉强的微笑。她不再戴着帽子,遮掩因传统疗法脱发后稀疏的头顶,第一次戴上了女儿给她买的一顶假发。女儿希望,假发能帮母亲做回“漂亮的女人”,母亲抗拒了很多次——这一次,她相信了。
“服用(全口服DAA新药)24周吧,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妈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什么,她都好像没听进去,现在她会拿着手掌跟我说你看,我鹅肝掌好像没了。那个时候我怀孕了,她也终于有心思
转载请注明地址:
http://www.fbmgc.com/zcmbwh/19898.html